
朱塞佩·托纳多雷是一个在电影院里成长起来的导演。六七岁时,这位未来的意大利著名导演第一次走进电影院,看见银幕上人物的大特写,觉得如同巨人一般。
“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?”托纳多雷问自己。
这一儿时的发问影响了他的一生。他开始在影院中寻找答案。从《天堂电影院》《海上钢琴师》到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,托纳多雷创造了诸多影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最近,作为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来到上海,托纳多雷依旧如孩童般充满好奇。“我心目中的天堂电影院,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。”他说。
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
1956年,朱塞佩·托纳多雷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,16岁时正式涉足电影行业。他是导演、编剧、剪辑师,也是小说家和摄影家,用现在的话来说,是位不折不扣的“斜杠青年”。最初的摄影师的履历,对托纳多雷的电影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而在此之前,他还有一重“隐藏身份”,藏在他的代表作《天堂电影院》里——电影放映员。
 《天堂电影院》海报
《天堂电影院》海报
解放日报:《天堂电影院》的剧本是如何创作的?
托纳多雷:我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,脑子里面已经在酝酿《天堂电影院》的剧本。经过11年酝酿,我才真正把这个故事写出来。
当时已经定了这样一个主题,讲小乡村的电影院,后来它关掉了。我记忆中有很多生活素材,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后来有一次遇到《百年孤独》的作者加西亚·马尔克斯,我们对谈的时候,他跟我说了一句话:“当你脑子里面开始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候,你不要马上写,你就去想,你越想这个故事会越丰满。”所以,11年来,我脑子里边一直在构思这样一个故事。当我开始提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,大概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就写完了。完成写作以后,我没有再和其他编剧合作,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独立完成的事情。
解放日报:你很小的时候就好奇电影是如何被放映出来的?
托纳多雷:我第一次进电影院的时候,大概六七岁,当时灯都关了,就看到银幕上面人物的大特写,看起来像个巨人一样。我一直在问自己,这些巨人是从哪进来的?我还去看旁边的门,看看他们是不是从那个门进来的。中场休息的时候,灯光亮起来,这些人又都消失了。
当时所有人都在吸烟,整个电影院里雾蒙蒙的。我看到放映厅有一束灯光照在银幕上,它动的时候,人物也会动,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,这里边的秘密一定藏在小窗口背后。
 朱塞佩·托纳多雷
朱塞佩·托纳多雷
解放日报:后面怎么知道小窗口后面的秘密?
托纳多雷:当时我认识了第一个电影放映员,他既是电影放映员,同时还是一个摄影家,他教会我放映电影,也教会我摄影。我做摄影师做了很多年,到现在为止,还是非常喜欢拍照片。我也学会了放电影这个技术,到现在也还会。在我自己的办公室、家里边,我都有放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,时不时还是会放一下。后来我又认识了其他一些电影放映员,把他们结合在一起,就出现了《天堂电影院》中的阿尔弗雷多的形象。
解放日报:你大概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驾照,白天去上学,回来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,这段经历对你了解电影有什么帮助?
托纳多雷:童年那一段时间,日子过得非常充实,我也非常忙,白天去上课,夏天放暑假的时候,就给人家拍照片,这样可以赚点钱。平时上午上课,下午去电影院做放映员,放映电影的时候,我就研究胶片、研究剪辑是怎么做的。我把自己的8毫米胶片机放在旁边,自己拍摄的东西也放在那里,这边学会了怎么剪辑以后,对自己拍摄的东西尝试进行剪辑。这样,我就学会了做剪辑。
我发现,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我想跟所有学习电影的人说,你不要止步于只学一样东西,你应该多方面地去学,尤其是剪辑。我自己在做《幽国车站》的时候,整个后期剪辑工作都是自己做的。我的绝大多数电影,都不会用专业的剪辑人员帮我做剪辑,都是我亲自来做。
 这次,托纳多雷作为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来到上海
这次,托纳多雷作为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来到上海
解放日报:你当时很年轻,从一个乡下地方来到大城市,开始拍电影,这个机会是哪里来的?
托纳多雷:我一直都挺努力的,努力很重要。同时,我挺幸运的。26岁、27岁的时候,刚好罗马的大导演来到西西里岛拍片子,拍一个关于黑手党谋杀题材的电影。拍的过程当中,他发现超预算了,得削减费用。后来有一部分工作转包给我,让我拍摄完成一些片段。
这个片子完成以后,制片人很高兴,因为没有超预算。我也被介绍给了这位制片人,他还蛮欣赏我的作品。等我要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,就找到这位制片人。他没有一下子就投我,他只是说,你先把剧本搞好,拿剧本我来看一下,我认为这个剧本好的话,我就会投钱来拍你的电影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坚信,你要去努力,你要全情去投入,去深入学习知识,去学会做你的事情。你一直很努力的话,总有一天幸运会来敲你的门。
反复出现的“西西里”
作为新现实主义浪潮后极具辨识度的意大利导演,托纳多雷以魔幻笔触解构现实困境的艺术特质,赢得了“影像魔术师”的美誉。在其跨越四十余年的创作图谱中,“时空三部曲”(《天堂电影院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)犹如三棱镜般折射出导演对时间、记忆与存在的哲学思辨,构成世界影史中璀璨夺目的艺术坐标。
对托纳多雷而言,意大利是他的故乡,也是他的电影所始终注视的方向。他有一个朴素的原则——做电影,要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、看得懂的电影,这样的电影才算“经典”。他也很开心观众能有不同的解读视角。每当有观众提问他电影中的细节,托纳多雷总是眼前一亮,继而兴奋地说:“我很喜欢你的问题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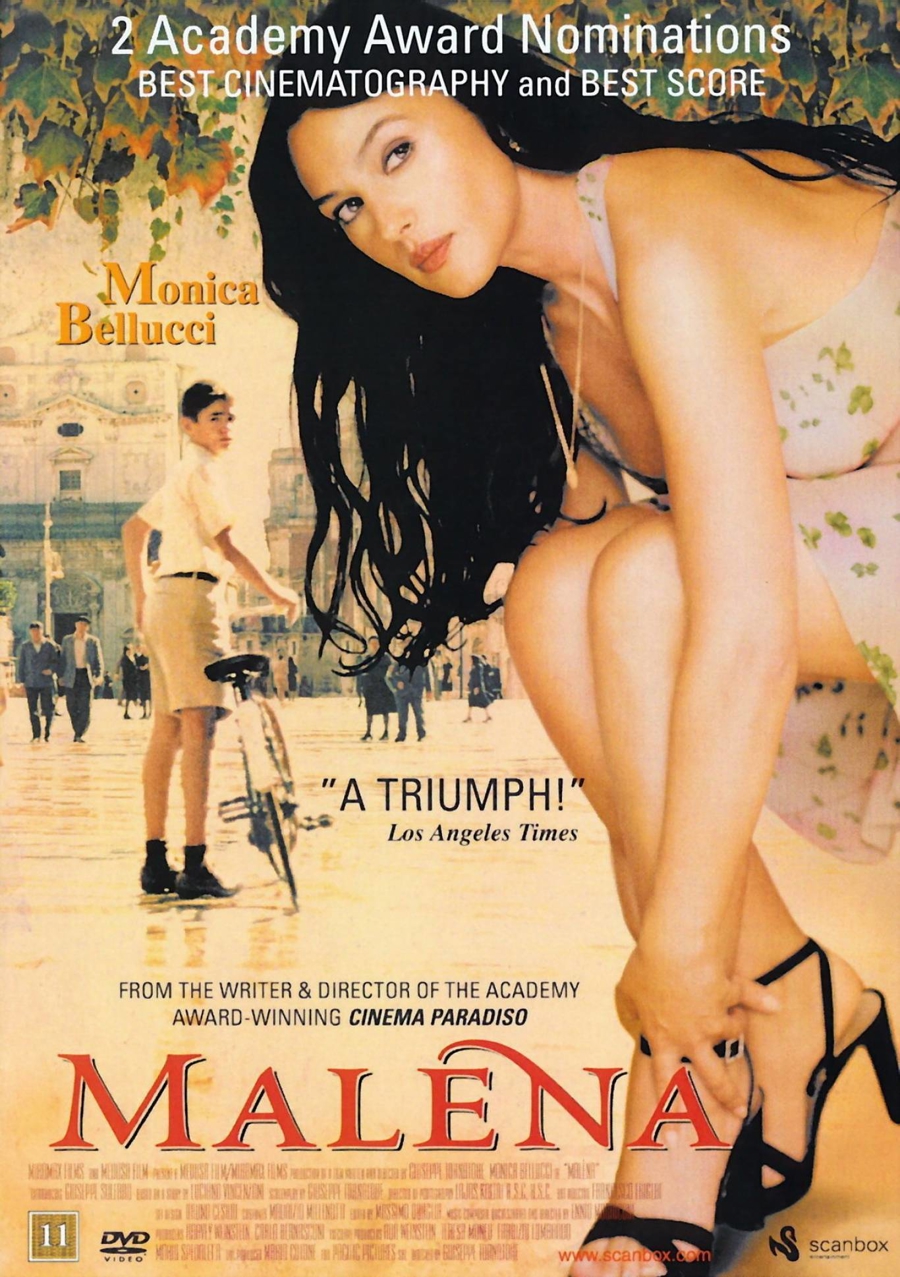 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海报
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海报
解放日报:西西里在你的电影里反复出现,你觉得这个地方带给你和你的电影最大的影响是什么?
托纳多雷:我出生在西西里,我在西西里工作到27岁,然后移居到罗马,在罗马已经生活了40年,我也把罗马看成是我自己的城市。
作为一个在西西里出生的意大利人,意大利就是我的国家。我所有的想法,还有我对待所有事情的方式,就是典型的意大利的方式。所以,关于在意大利的故事,在西西里发生的故事,会反复地出现在我的电影中。于我而言,它是我的文化,代表的是我的故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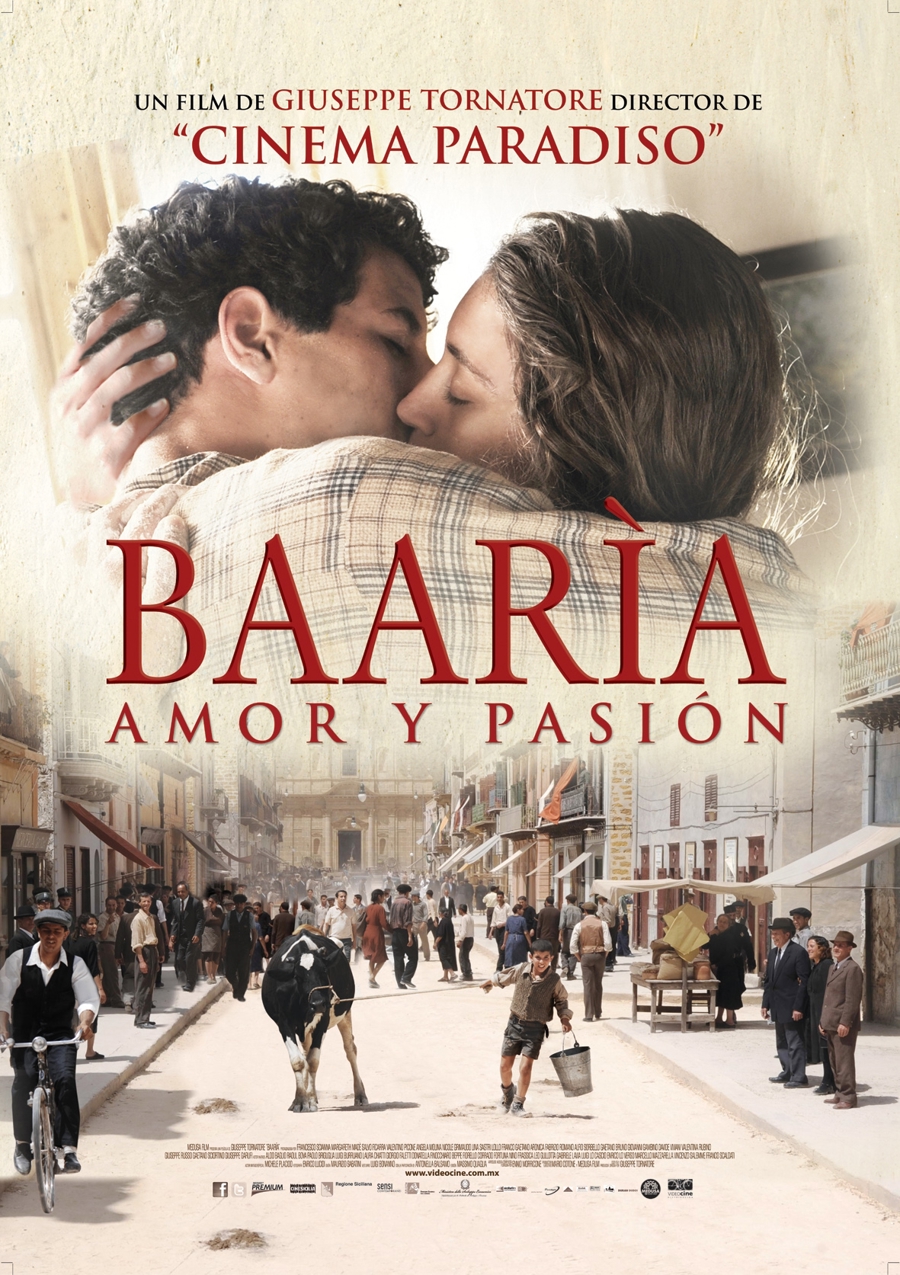 《巴阿里亚》海报
《巴阿里亚》海报
解放日报:《天堂电影院》是用纯正的意大利语来拍摄,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用了能听得出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语来拍摄。但有一部制作费用非常高昂的《巴阿里亚》,用的是你童年生活的小镇的方言,许多人听不懂这种方言,当时是怎么说服制片人的?
托纳多雷:《巴阿里亚》这部电影,我在写剧本的时候,就是用我出生的小镇的方言来写的,我只能用方言去写。制片人读这个剧本的时候,他脸都变白了,因为根本读不懂。这个电影讲的是这个小镇的故事,用当地方言来拍看起来非常自然。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,一个版本完全用谁也听不懂的方言来拍;还有另外一个配音版本,配的是有方言口音的意大利语。
实际上,我的所有电影,西西里都是深刻烙印在里边的。如果说《天堂电影院》是一个自传体类型的故事,那《巴阿里亚》则是一个真正的自传体的故事,它讲述的是我的家庭的故事,讲述的是我小时候出生、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。整部电影让我们投入了太多感情,在它拍完以后,我应该不再讲西西里了。
事实上,我还拍了很多不是发生在西西里的电影,但我发现那一份归属,那一份情感是割舍不掉的。很多电影不是发生在西西里这个地方,但实际上里边所蕴藏着的西西里的元素,比真正发生在西西里的故事还要多。
 朱塞佩·托纳多雷
朱塞佩·托纳多雷
解放日报:拍电影时,你有自己特别遵循的原则吗?
托纳多雷:我是一个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,从小接触观众,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,就非常清楚,如果要用一部电影去讲一个故事,一定要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能够很容易去理解。我的一个原则是,做电影,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、看得懂的电影故事,这样的电影才是经典。
我在做导演的过程中,只有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违背了这个原则,就是《幽国车站》。那部电影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,因为很多人看不懂。肯定是看不懂的,我拍的时候就知道。因为我很喜欢,我很想尝试,所以我就拍了,它的票房并不好。但时隔这么多年以后,那些真正爱电影、懂电影的人,还是能够接受观众看不懂的电影。
总之,用真诚的心态去讲故事,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,观众更愿意去走进你的电影。但这也不是保证你的电影可以获得成功的唯一方式。《天堂电影院》实际上是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的一部电影;而在《海上钢琴师》的故事中,很多东西也折射出了我的人生。
 《海上钢琴师》海报
《海上钢琴师》海报
解放日报: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、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。作为导演,在你看来,电影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?
托纳多雷:在超过百年的历史中,我一直认为电影的诞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成就,而不单单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影的诞生。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想象,没有电影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。
在这130年中,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?可以说变化很多,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变化。说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是因为拍摄电影的技术、成像的方式、清晰度等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说电影什么都没变,是因为从它诞生那一刻起,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没有变。在电影诞生的最初10年间,它所具有的所有潜质都已经开发出来了,那时就有科幻电影、有讲述真实故事的电影、有政治题材的电影、有犯罪题材的电影,还有历史题材的电影。130年中,我们还是继续讲述同样的内容,同样的故事,只是技术发生了变化。
电影必须存在
此次上海之行,托纳多雷对一切充满好奇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,除了参与电影评审、大师班、见面会活动,他也带着浓厚的兴趣探索上海。他在上海的逗留时间很长,除了去豫园Citywalk,还有不少私人行程。6月15日下午,托纳多雷造访大光明电影院,当时,千人厅在放映陈可辛导演的《甜蜜蜜》,全场坐满。他饶有兴致地看了十几分钟,还掏出手机,悄悄拍摄了现场观众认真看电影的情景。
那几天,在大光明、国泰、兰心大戏院等老影院,托纳多雷爱上了甜甜的爆米花。他还去了外滩、上海历史博物馆参观,到武康路、五原路、星光摄影器材城、浣熊唱片上海影城店等地方打卡。不少影迷在上海街头偶遇了托纳多雷,并获得签名。
什么是好电影?如何拍好电影?电影的未来在哪里?来到上海,托纳多雷向影迷、媒体和电影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,而经历了这场上海之旅,对于这些问题,他或许也有了新的答案。
 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
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
解放日报:你有比较喜欢的中国导演或中国电影吗?
托纳多雷:有好多中国导演,我都非常尊重,像王家卫、张艺谋、陈凯歌、陈可辛等。中国的电影真的非常美,张艺谋导演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这部电影非常美。我在1991年第一次看,就喜欢上它了。我看到,近十年中国的电影发展非常迅速。这几天我真的有太多的欣喜。
解放日报:作为一个意大利写实派导演,你在近70岁的时候,选择参与中国科幻电影《带上她的眼睛》,是否也是在寻求创作风格的改变?
托纳多雷:应该说,在我的整个导演职业生涯中,我一直是在变的,我的电影风格也一直在尝试变化,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。科幻电影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,只不过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出发。在整个创作过程中,其实我是非常享受的,我也觉得很好玩。
解放日报:今年是中意建交55周年,你觉得电影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?
托纳多雷: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,每一部电影实际上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创作。比方说,我在和中国方面合作来写科幻的剧本时,这种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地了解和交流,这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。中意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,也希望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能一直进行下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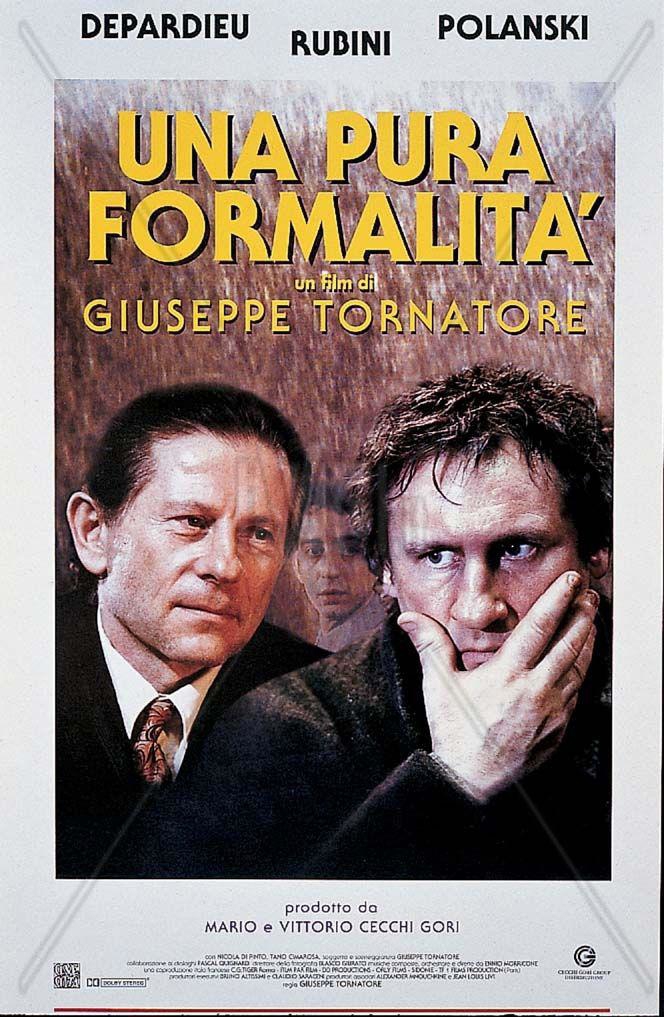 《幽国车站》海报
《幽国车站》海报
解放日报: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有更多合作项目?
托纳多雷:首先,我是一个电影观众,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导演。所有机会来临时,我都会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。可以借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的电影人和制作体系,这种想要和不同文化接触、合作的好奇心一直有。我特别喜欢中国,如果有机会来这里拍电影,我是非常期待的。
解放日报:这次来中国和以往有何不同之处?
托纳多雷:我来过中国好多次,从来没来过上海,每次来中国都会带着美好回忆离开。上影节也多次邀请我来参加,之前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有时间,但这次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来,我非常高兴能接受这样的邀请,来到上海,有机会接触、认识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。
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。我有一个执行制片人,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,一直跟我讲述各种各样的中国见闻,一直能激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。他也一直跟我说,你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。2006年我在中国逗留非常久,那次是来拍摄北京奥运会宣传短片。所以说,我一直对中国的文化深深地着迷,也很想能够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。
 朱塞佩·托纳多雷
朱塞佩·托纳多雷
解放日报:现在全球电影市场其实是在走向一个相对下滑的状况,你认为电影人包括电影本身应该怎么去对抗这种下滑?
托纳多雷:尽管大家都在这样说,但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电影、新的电影人,也会有一些新的电影收获很大的成功,比如《还有明天》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的状况下制作出来的新电影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电影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,本质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。
在这种情况下,电影人应该做什么?我们要相信电影产业,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电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坚信。另外,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,同时也要勇于去尝试采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创作。
当我说到电影人的时候,我不仅仅是说导演、编剧,还包括所有的投资人、所有大的社交媒体平台,你们都必须要坚信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电影。不要被眼前的工业发展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所困扰。电影必须存在,也一定会有很多机遇。
解放日报:作为一名导演、一名观众,你看电影时有什么期待?
托纳多雷: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,我不想怀着特定想法或者期待去看电影。但我每次都希望电影能给我带来一种惊喜。进入电影院,所有灯光关闭,我作为一名观众,不会带着评价电影的方式去观看,而是一种电影体验。看电影时我会全情投入,深入了解内容,希望能够有所启发、学到东西,这是我每次去看电影时的期待。
朱塞佩·托纳多雷
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,他曾凭借《天堂电影院》获得第42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,凭借《新天堂星探》获得第5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,凭借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入围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。
炒股股票配资网站,最安全的配资平台,在线配资论坛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